其實我也是紅二代
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2月26日。今天晚上我做了一檔特別節目!
爲什麼今天晚上要做這個特別節目?因爲今天這個日子對於我個人來講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所以我選擇在這個夜晚做一檔特別的節目,把它獻給我的父親。因爲今天是我父親的生日,是我父親的誕辰90週年!很長時間以來,我經常想念到父親,每次他的音容笑貌都出現在我的腦海裏面。今天在他90歲誕辰的日子裏,我十分懷念他。所以我今天就做一檔節目來紀念我的父親。
如果給今天的節目起個名字的話,應該叫做《其實我也是紅二代》。爲什麼這麼說?中共劃分紅二代,是根據四九建政這個日期來劃分的。只要你是在四九之前參加中共的,中共就算你是開國建政的那一代,那麼他們的子女就算是紅二代。中共建政的時候有幾百萬將士,這些人都是所謂的紅一代。但是大部分的這些所謂紅一代,他們基本上在中共建政以後經過朝鮮戰爭,經過中共的歷次運動,大部分人被整死,鬥死,以及身體不好病死。真正活到80年代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時候,在這也是改革開放中能夠獲得機會的,是那些開國元勳的兒女。普通的這些中共建政前參加革命的人的子女,他們大部分是輪不到這種機會的。等到陳雲和鄧小平要培養紅二代,培養這些中共建政前官員家的子女的時候,這個時候還能夠活著,還能夠有機會,並且在中共的官僚體系裏面能夠給自己的子女說上話,能夠摸到機會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少了。所以說如果按中共四九建政來講,不是所有的什麼紅二代兒女都有像習近平和薄熙來這樣的機會,能去擔任什麼中共的高級領導人的。
今天是12月26日。我父親很巧,正好出生在12月26日。老一點的中國人都知道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所以在過去我們很小的時候,經常因爲那毛澤東在12月26日要求全國人民吃麵條。那時候大家都要吃長壽面,所以每一次到12月26日這個節日,我們家裏面也會吃麵條,只是我們的這些麵條是給我們父親祝壽的。因爲我父親恰好跟毛澤東是同一個生日,所以爲了這件事,在文革時候還有一些軍隊中的左派質問過我父親,你憑什麼跟毛主席是同一天出生的?在我的記憶中,每天12月26日這一天,我母親都會準備好麵條,讓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都坐下來爲父親吃一碗壽麵。父親如果活到今天,就是90歲,但是他離開我已經十來年了。
我的父親是民國時候出生成長,他在抗戰結束之後,在上海選讀了醫科學校。他在醫科學校還沒有畢業,還在實習的時候,有一次爲他的診所來了一位傷員,這個傷員爲很重要。當時我父親並不知道他這個人的身份有多麼重要,只是不斷看到有很多有錢人和有關係的人來打招呼,來幫忙,讓他的病能儘快轉危爲安,徹底治好。後來爲他的病情穩定了以後,我父親所在的那個診所的醫生帶著我父親一起把他護送到他講的一個地方。結果我父親到了那個地方,才知道他實際上是共產黨軍隊裏面的一名高級幹部。我父親到了這支部隊以後,當地的官員就把我父親和那個醫生統統留下來了,他們就不讓我父親和那個醫生再回去。他們的理由是:你們過來了,你們的身份已經暴露了,你們再出去被抓住就肯定有生命危險!現在你們只能夠暫時留在部隊裏面。這是他們的理由,但實際上的他們是需要醫生,因爲他們太需要有能力的醫生了。就這樣,我父親就留在了這個二營,因爲他是醫生,所以他承擔了軍醫的工作。
那個時期還是戰爭年代,二營在參加了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之後,我父親這支部隊一直打到了海南島。當時我父親跟我講,到了海南島的時候,他們那時候沒有別的飯吃,就是吃魚。每天的飯就是魚,魚就吃飯。而且這些魚腥得不得了,一股魚腥味。就是那次吃魚就把我父親吃搡了,也就是頓頓吃魚吃得上吐下瀉。而且當時船在出海,每個人都在吐。他作爲一個醫生還要救活別人,他自己都扛不住。所以我父親對魚,對魚腥味就有一種天然的反射,一種反感,因此我父親後來把整個一生都不再吃魚。
我父親參加中共軍隊,他是吃了很多苦的。包括中共剛剛建政的時候,在四九建政還沒有開始,10月1日還沒到的時候,我父親的這支部隊就已經被安排進藏了。他告訴我,進藏的路那簡直是比當年紅軍長征走的路還要難。因爲要面對所有的自然災害,那種根本不適合人居住地方,連騾子和馬都走不了的地方,部隊要行軍。當時是過雪山,我父親是軍醫,在一路往西藏進發的過程中,有很多人堅持不下來,最後摔倒在路上死掉了,在雪地裏。因爲非戰鬥減員特別多,他們當時走的時候只有一個團,他們團裏面的領導人規定,任何人倒下,另外的戰友不能扶。因爲一扶你也就死了!所以說我父親完全是拼體力,完全拼意志,也就是自己要跟著隊伍走,一旦掉隊就是沒命。而且你一旦倒下,沒有人會扶你。就這樣,我父親走過了他自己艱難卓絕的進藏路。
他們到達的時候,當時18軍軍長張國華的部隊根本還沒有進藏,是他們這個團先去打了先鋒。之後,我父親隨這個團撤了出來,撤到了雲南昆明,所以我父親的老部隊都駐紮在雲南昆明。我父親隨著進藏的部隊回到昆明以後,在昆明休整了一段時間。這時候部隊已經已經開始了結束戰鬥,已經開始了進入城市管理。部隊裏面的很多軍官都已經轉移到地方,在地方上擔任高級領導職務。而我父親當時仍然留在部隊!那時候他還很年輕,而且曾經上過醫科學校。雖然他的實際文化也就是個高中生,但是部隊裏面還是想培養他,最終他們軍區裏面就決定從昆明軍區選送三個人到重慶第三軍醫大學,讀正規的軍醫科班。於是我父親他們就帶著部隊開的介紹信,他們三個人就結伴從昆明向重慶進發了。
去重慶的路上,仍然是走了很長的時間。那時候沒有條件!我聽我父親講,牛車馬車都坐過。最終等他們到達重慶第三軍醫大學的時候,人家都已經開學了。我父親跟我說,他當時拿著介紹信到教育長的辦公室,跟教育長講我們是來報導的,我們來自昆明軍區的,有昆明軍區的介紹信。教育長看了介紹信之後,就說沒辦法,我們學校已經開學了,現在每個班級的人都落實了,現在真的是沒辦法把你們再插進去。因爲只有那麼多位置!你們就在部隊的招待所裏面休息,等到明年開學再上。我父親跟我講,當時已經大概是11月份左右,如果是明年再上的話,那就意味著耽誤將近一年的時間,所以他們當時就想,我們能不能回去,明年再來。那個領導就跟他講:你回不去了,你看你們這一路來都來幾個月,你們回去要幾個月,到了那邊然後在過來,這樣在路上走有意思嗎?這樣吧,我給你打電話聯繫聯繫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看看他們還有沒有學員的位置,如果有的話我把你們轉到那邊去。我父親他們幾個人都很願意,因爲顯然上海比重慶更繁華,在他們心目中更希望能見識一下上海。於是那位教育長就給他的老戰友,也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教育長打了電話。
結果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告訴他們,我們元旦才開學,你們馬上過來的話完全來得及,這幾個位置我們給你留著!就這樣,我父親和他那兩個戰友一起從重慶坐船來到上海。這次速度就快多了,因爲從重慶坐船到上海不要多少天,大概就十天半月他們就到達了上海。這樣,我父親就進入了上海第二軍醫大學讀書。他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完成了他的大學本科學業,讀了五年的醫科。在第二軍醫大學裏面,它奠定了我父親整個他未來的一生成長的道路。因爲在學校裏面,他的班上有一個會講俄語的女同學。這個人是誰的?這個人的中文名字叫翟雲英,但是她在大學裏面大家都喊她叫劉素娥。爲什麼叫劉素娥?因爲是一個俄國人,不是中國人。但是她有一個顯赫的身份,他是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的太太!她當時也在第二軍醫大學進修。他和我父親在一個班,而我父親恰好是這個班上唯一會講俄語的同學。當時在學校裏面要求,醫科學生儘量學會一門外語。那時候對英語沒有那麼高的要求,而中國那時候跟俄國關係很好,我父親自己也比較用功,所以他的俄語說得不錯,因此他跟劉素娥交流比較多。雖然她在學校裏面大家都叫他劉素娥,但是實際上她起的中文名字叫翟雲英。
到了大學畢業時候,劉素娥勸我父親跟她一起到北京去,到空軍去。如果我父親沾了他這位蘇聯同學的光,可能能夠到北京去工作。但是我父親沒有同意去,因爲他原來的老道長已經調到了海軍,非常希望我父親能到海軍來。就這樣,我父親從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畢業以後就來到了南京,在南京海軍學院工作。南京有一所海軍高級指揮學院,這所學院當時的海軍的最高學府,這所學院的院長和政委,都是我父親當年的老首長。而這兩個首長都是中共最年輕的將軍之一,他們當時都非常年輕。這兩個人都是江西興國人,1955年授軍銜的時候,因爲他們太年輕,所以毛澤東認爲他們不能夠擔任他們跟職務相當的軍銜。因爲海軍高級指揮學院是兵團級單位,他們兩人作正兵團級,是最起碼要授予中將軍銜的。但是這兩個人年紀太輕了,所以毛澤東說:雖然這兩個人革命資歷很老,但是他們年紀太小,給他們安排一個少將,未來還有晉升的日子。所以他們兩人是院長,政委,但是反而是少將。而在裏面的其他將軍年齡都比他們大得多!
我父親最終在這兩位老首長的手下開始工作。他經常提起這兩位老首長的名字,一個叫雷勇同,一個叫謝立全。雷永同是政委,謝立全是院長。在文革期間,我父親一直在這兩位首長身邊工作。文革爆發以後,這兩個人都受到了極大的衝擊,最終他們一個病死,一個被鬥死了。我父親當時那是保健室主任,負責首長和首長身邊的家人的各種醫療保健工作。當時他親眼見到這兩位老首長最終被折磨死,所以他的心情是很差的。那時候我還很小,還不是很懂這些事,但是我父親也很少跟我提起,我只是看到他大部分時間站在陽台上自己默默抽著煙。有的時候他回來看看我,他只能告訴我:你在家要注意安全。爸爸不是每天都能按時回家的!這兩位首長去世以後,我父親就被調整了工作。
我父親被安排到了南京軍區的徵兵辦公室擔任體檢軍醫主任。而這個工作爲是一個聯合招生辦,是江蘇省軍區設定的一個爲整個南京軍區每年徵兵所安排的這麼一個辦公室,我父親後來就到了湖南路江蘇省軍區的這個徵兵辦的體檢辦公室工作。這時個候,我父親他應該來說權力很大。因爲大家都知道,在文革期間,絕大部分的這些所謂幹部子弟都是送到部隊去培養,而且很多幹部那時候都受到衝擊,很多幹部在他們手上還有點權利之後,他們都希望能夠把自己的子女早一點送到部隊去。或者有的老幹部已經受到衝擊,他們就希望他們還在職的老戰友能夠把自己的兒女送到部隊去。因爲送到部隊,他們認爲至少是給了兒女一個紅色的保險箱。而我父親負責徵兵工作,負責體檢工作,所以我父親是有著絕對權力的。因爲大家都知道,那時候當兵要求第一是根正苗紅,第二是身體健康。而基本上能夠有資格在那個年代進入部隊的,大部分都是根正苗紅。而身體健康不健康,那就是軍醫主任說了算。如果我父親不同意這個人去當兵,說他身體不合格或者不符合徵兵的體檢要求,那他就怎麼樣都去不了。所以在那個時候。每天來找我父親寫條子的老首長,打招呼的老戰友多得不得了。我父親可以說是應接不暇,他也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事情。但是他告訴我,大量南京軍區的高級幹部家裏面的兒子女兒,有的年齡都很小就把他送到部隊去了。因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也希望保護好這些老首長的子女。因爲很多老首長那時候都在捱整,他希望把這些子女送到部隊去之後,至少讓老首長自己的兒女有個好的安排,他就心安了。
記得有一次父親在家裏面跟母親提過,他跟母親說:“不如送建民去當兵吧。”母親說:“怎麼能送建民去當兵?”父親說:“首長們家的子女統統都去了,有的都是14歲15歲,建民也是十四五歲,這個年齡也差不多了,也可以去!”母親回了他一句:“你不是首長,我們家的孩子還小,我們孩子也吃不了這個苦,還不得,在部隊我們也沒有這樣的關係。你的那些首長家的子女在部隊自然有其他首長幫著照應!”父親當時就是反對我父親在我年齡很小,只有十四五歲就把我送到部隊。當時我確實太小!但是很快文革就結束了,文革結束後整個80年代是中國最好的十年。這十年,整個中國都是在人人向上。那時候我父親也基本上是煥發了他自己思想上的青春。但是他的年齡已經大了,那時候他已經失去了在部隊裏面得到提拔的機會。雖然80年代鄧小平那時候搞政治化,軍事化,科技化,年輕化,也就是部隊裏面的四話。我父親前面幾化都符合,就是不年輕了。因爲到了80年代,我父親他已經過50了,根本就沒有提拔的可能。但是我父親那時候一心一意希望給我創造上夜校的機會,或者給我有更多的深造機會。我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就就堅持要把我送到部隊去。那時候我已經十八九歲了,母親這次就沒有再阻攔我父親,所以我就到了海軍航空兵部隊。
等到我從部隊裏面退役之後,那時候我父親就非常希望能給我找到一個很好的職位。因爲我們那時候從部隊下來之後都是分配工作的,但是大部分分配的單位都很不好,我父親希望能給我找到一個好的單位,能給我再創造一個讀書的機會,讓我早點進入高校去深造。他一心希望我自己能在年輕的時候打下一個良好的高校讀書基礎,爲了可以鍛煉成才。我想這也是天底下所有父母他們的一個心願!所以爲了給我找一份好的工作,我父親就去求他的老戰友,包括很多當年給他送入部隊,已經在部隊裏面鍛煉成長,現在已經有了一定職位的一些官員。有的人從部隊裏面早就轉業下來,在地方上已經擔任了比較重要的職位。這個局的局長,那個局的局長,包括在鼓樓區民政局的那個副局長就是我父親當年把他送到部隊的,他也是軍隊的一名幹部子弟。我父親也去求過他!每一次我父親帶著我去參加所有的這些幫助我找工作的這些吃喝會議上,我看到父親給他們拎著煙,拎著酒向他們陪笑臉的時候,我心裏面是非常非常難過的。我坐在旁邊,我真的是不願意父親爲了我這樣去求他們。但是我父親那時候希望我能夠懂他的心,所以我每次陪著他去,爲了幫我找工作,看著他拎著酒拎著煙跟別人陪笑臉,我心裏真的很不是滋味。
好在我父親有一個老戰友給他非常鐵桿兒,他的兒子在一個單位裏面擔任人事科長,把我弄到了他她所在的那個企業集團,我也在這個集團裏面弄到了比較好的一個職位。等我到人事科報到的時候,才發現整個人事科裏面全是女生,而我這個科長是這個科裏面唯一的男生。他告訴我,咱們整個科你來了以後就有兩個男生了,所以很多髒活累活你得先幹著!所以那時候我每天都在發奮學習,晚上就到夜校,終於讓我那就考上了江蘇省的商業學院(現在叫江蘇財貿學院),也就是因爲進入了這家學校學習,讓我遇到了八九六四。
1989的的那一年正好是我畢業的一年,結果在1989年全國爆發了六四學潮,這個六四學潮從北京一直影響到了南京。我積極參與了六四學潮之後,後面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鄧小平在北京痛下殺手,用機關槍和坦克車對學生和北京市民大肆屠殺。這時候,我的父母親就非常非常緊張。尤其當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江蘇省和南京市在通緝我的時候,我父母親那時候心裏面真的是非常悲傷。因爲他特別怕我被抓住,被共產黨弄去坐牢,甚至還想到了文革時候。當時他已經作好最壞的打算,我都不一定能活著出來。
很快,我就被中共抓捕,然後進了監獄。在進入監獄的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的案子是不審理的,我們就是在看守所裏面關著,我當時被關了很長時間。一開始我和我的幾個同伴都被他們關在軍隊的看守所裏面,關在南京軍區西善橋政治部的看守所,我和我其他的六四同學完全是分開關押,我大部分參與南京學潮的六四同學當時都關押在南京市公安局茶亭的看守所裏面。我是知道一年半以後才和我其他幾個同伴從部隊看完所把我移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茶亭看完所。到了茶亭看守所以後,我們始終是在等待審判狀態,一直到1991年夏天我們的判決才開始。等我們的判決生效以後,看守所就允許家屬探望了。我父親在那時候有很多戰友都在公安系統和監管場所工作,他也跟他的一些戰友打聽過,人家就告訴他,你兒子的這個是政治事件,誰都不能碰,誰都不敢幫你,只能講如果法律允許你可以探視的時候,我們會給你安排一次探視的機會。現在終於等到這個機會,也就是我在被關押兩年左右以後,我第一次在看守所裏面見到了我的父母。那天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我的鐵牢牢門突然打開,我們那邊的管教喊了我的名字。他告訴我,你的父母來看你了。他帶著我從走廊上一直來到了他們那邊的接見辦公室。
在那裏,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弟弟妹妹,還有幾個我在南京高自聯的同學。這兩個同學都是沒有被判刑,沒有被拘捕,因此他們以我們家裏面的親屬混進來了。而還有好幾個南京高自聯的,我當年的戰友,他們因爲都在這個看守所被拘押過,那時候他們雖然已經放出去了,他們也想來看我,但是都被這裏的管教攔在外面,因爲我們這邊的管教認識他們。按照看守所的規定,是不允許以前在這邊在押過的人回頭來探監,探望其他在押人員,所以他們都不能進來。那一次,我對我父親的回憶記憶猶新。我父親用手摸著我的頭髮,沒有說話。他只是問我:“兒子,還好嗎?”我說:“爸,一切都好!”那一次接見的時間很短,我媽哭得像個淚人,而我那次最記得的,是我感覺到我父親有非常非常多的的話要跟我講,但是他沒有說。
就這樣,我在看守所裏面就被轉換到勞改隊,我記得我是冬天很冷的時候被送到南京市郊區的江蘇省龍潭監獄。當時龍潭監獄執行了省裏面的一個指示,也就是把全省所有的反革命重犯全部押到了龍潭監獄的一個叫金工二的車間,他們簡稱叫二金宮。很多人一聽到二進宮就以爲是犯人第二次被關進來,叫二進宮,社會上都是這麼說。但是在龍潭監獄,只要講二金工,大家都知道那叫金工二車間。那是最嚴的的一個車間,全部是重犯,而且大量都是反革命犯。我去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這個金工二車間有幾百號犯人,而且這幾百號犯人裏面有將近一半以上的都是反革命犯,並且大部分是重刑犯,就是判十年以上的,15年的,無期徒刑的很多。我們大家知道,去年已經被共產黨折磨死在牢房裏面的楊天水,他的本名叫楊重陽,他就跟我一起關押在這個車間裏面。老楊比我早幾個月先關在這個監獄,我去了以後,和老楊共同在這個監獄裏面度過了很多年的時光。
在我被羈押的那段時間裏面,我父親我母親每個月都來探望我。他們表示,只要允許來看,無論颳風下雨,我們都會風雨無阻的來看你。他們每次給我帶來一點葷菜,帶來一點水果,也給我帶來一些報紙,讓我能瞭解外面的訊息。那時候監獄裏面的近視條件還不像現在那麼正規,那麼嚴格,有那麼多電子設施,那時候我的父母親跟我還能坐在一條板凳上。我記得有一年父母親來看我,當時我父親拉著我的手,他問我:“孩子,他們打你了嗎?”我說沒有。我爸就跟我說:“爸是當醫生的,你覺得爸看不出來嗎?”我就跟我爸說:“爸,都過去了,我都堅持過去了!”我爸緊緊的攥著我的手:“孩子,爸多麼想代替你!”我每次想到這句話的時候,我都想到我爸深情看著我的眼光。
我父母每次來看我,都要花上整整一天的時間。因爲那個時候的交通很不方便!我父母要從我們家所住的地方坐長途汽車到南京的堯化門,然後從堯化門再轉郊區的班車。而這個班車一天只有一班,就是上午9點半,他們必須要趕上9點半的這班班車,從堯化門再到龍潭,路上又要一個多小時,他們到達我這裏基本上在10點半左右,所以往往他們在10點半左右才排上隊。至於什麼時候能見到我是沒數的,快的時候可能11點半到12點,慢的時候可能要等到下午3點,因爲探監的人也很多,大家輪流排。
我父親在那個過程中從來沒有再去麻煩過他的戰友,因爲所有的戰友都躲著他,人家都怕在政治惹到什麼麻煩。因爲人家說:你兒子吳建民是重犯,是反革命犯,因此我們誰也不敢沾染這個!我父親心裏面很明白,他從來沒有去給他的戰友帶來過任何麻煩。因爲我父親是軍隊的高級幹部,是正師職,大校職位,在他在離休以後,按照軍隊的規定,他可以每個月使用車輛,也就是說師級幹部是有車馬費的。我父親他一開始是想申請這個車,每個月把他用車的機會用來探望我。結果在開黨小組會議的時候,其他的老幹部在一起批判他,都說他培養了一個反革命兒子,都說他培養了一個妄圖推翻共產黨,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兒子。“你養出一個反革命兒子,你憑什麼還用我們部隊的車去看他?你還要用自己的特權!”他們是這樣譏諷我父親。所以我父親很有骨氣,從此以後一次都沒有在部隊裏面叫過車,他每次就是跟我母親自己坐長途班車來看我,沒有用過部隊的車。其實他完全可以用,可以理直氣壯地用,沒有人有資格不給他用,只不過有一些人對他冷嘲熱諷而已。但是我父親他就是這個骨氣!
母親告訴我,在黨小組會議上很多人批判父親,很多人叫他做檢討,很多人要求他深刻地檢討爲什麼培養出這樣一個反革命兒子。我父親告訴他們:“兒子大了,兒子有自己的志向,兒子走的路跟我們當年參加革命走的路是一樣的。兒子的理想是爲了這個國家好, 是爲了這個黨好,是爲了這個國家有民主進步,我不可能決定兒子的政治人生!”我父親就這個態度,從來就沒有向他低過頭。當然我父親也很自覺,就不再使用他們的車輛。按我父親的話講:咱不佔公家的便宜!就這樣一直到我出獄,我父親和我母親風雨無阻,每個月都來看我。是父母每個月來看我給了我巨大的精神鼓勵,也讓我戰勝了無數次的困難,最終讓我活著從監獄裏面走了出來!
我記得我回來的那一天,省裏面把我叫到了江蘇省的華東飯店。在省政府對面,南京軍區的華東飯店,我們南京人稱它爲AB大樓。在那裏,省裏面的人跟我做了個約法三章,規定我回來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然後他們就給我父親打了電話,並且他們用一輛麵包車把我送回家。他們把車子開到我家附近的那個公交站台的時候就把我丟下,然後我自己回家。我沿著我自己熟悉的路走過我們家裏面的那個大院的時候,我就看到父親站在樹底下等我。我父親看到我過來了以後,他馬上就迎了上來。父親已經兩鬢斑白,他拉著我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著,問我:“孩子,回來了嗎?”我說:“爸,回來了!”父親拉著我的手:“孩子,把胸膛挺起來。咱們回家!”
父親邁著他堅韌的胸膛,拉著我,我們大步的走了回去。
每次想到這個情景,我就想到我對我父親是多麼的辜負。因爲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父親給我創造過很多次機會,但是我每一次都違背了他老人家的心願。當每次他希望我按照他指引的那條路走的時候,我總是違背了他的意志。回到家中的時候,我已經三十幾歲,卻只是一個刑滿釋放的人。我知道父親的那顆心傷得很重,但是父親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流露過一句他的悲傷。她總是告訴我:你還年輕,你要振作起來,你要自己去尋找你自己未來的道路。我希望你很快能夠自己安身立命!所以,我爲了不違背父訓,我自己很快就找到一個適合我自己在國內做的生意,於是就自己開始起步了。在這以後,我也成了家。但是因爲我不生活在南京,我只能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回家探望父母。沒想到父親的身體很快就倒下了!他沒能堅持到看到共產黨垮台的那一天,也沒能堅持到看到他兒子實現理想的那一天。
他走的那天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們老早早的就趕在病房裏面,那時候他已經氣若遊絲。他拉著我的手,他對我唯說的一一句就是:“建民,爸爸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他最終就走了,他帶著很多遺憾走,他沒能看到中共倒台的那一天,他沒能看到他兒子爲之奮鬥的理想實現的那一天。父親如果不走,今天已經90歲了,但願他老人家在天之靈能聽到兒子在他90歲那一天對他的呼喚。我多麼希望我自己有一天能大聲的告訴父親:我的理想實現了。中共已經垮臺了。他的兒子已經實現了他人生的理想!
雖然這一天到今天還沒有實現,但是我相信,我建民有生之年,我一定是能夠到達南京,到當父親的靈前再次叩拜我的父親。讓我的父親可以知道,他的兒子爲之奮鬥一生的理想,有一天實現了!
感謝大家的收聽.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做到這裏!謝謝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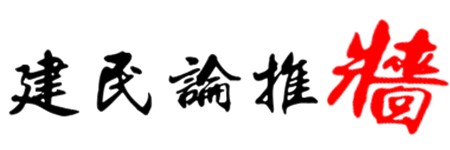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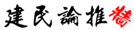



添加评论